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苦涩人生:
一个女人没有爱情,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
2020年10月27日 11:02:05
来源:在人间

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Duration 23:22
余秀华有两个月没写诗了,自己跟自己不高兴。 桌上的书,她也没看。 唯有床上那本《中阴闻教得度》经书,她忍着头疼还能翻翻。 这是一本讲念经、打坐、修行的书,“教人死了之后怎么送他上天堂。 ”
一张 1.8 米乘 2 米的双人床,成了余秀华离不开的地方。 每天,她待在床上的时间超过20 小时。 除了洗衣、吃饭、散步、浇花,她很少在地上活动。 不写诗也不看书的日子,她爱趴在床上看视频、下象棋。 她不怎么玩网络游戏,“吃鸡”半天找不到敌人; 她也不常上微博,不知道肖战是谁; 实在闷得慌,就开一场直播,跟陌生的网友说说话。
这段时间,她情绪不好,最严重的时候,一个礼拜睡不着。长时间的失眠,让她的眼睛“像扎着麦芒,有恶心之感”。夜半醒来,她会产生很深的恐惧感:“我不知道人活到最后是什么样。”一世的光阴,只能慢慢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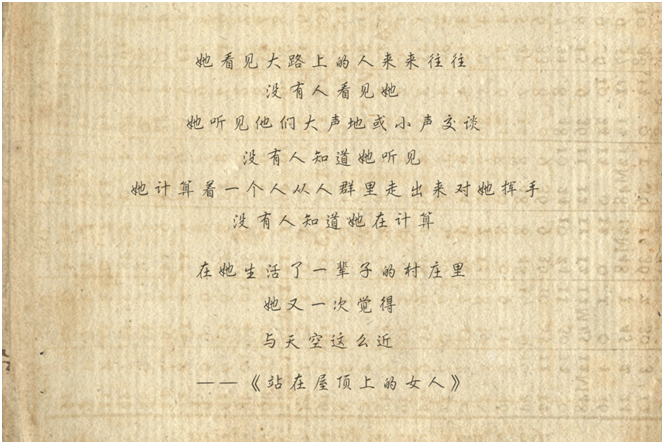
早上 6 点,天上的云雾还未散开,父亲余文海拎着家里的扫帚和簸箕,在主坡道上扫地。他红光满面,但劳动时胯受了伤,走起路来不太稳。
横店村——这座离武汉车程 3 小时的村庄,早已不是范俭当初拍摄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时的模样。2017 年春节前后,300 多户村民搬进了新楼。窄小的上坡路变宽,两边的稻田被一排排双层洋房替代。余家失去了 20 亩土地,余秀华也失去了看夕阳落下的四合院,唯一保留的是2 分地大小的鱼塘,由余文海打理。
新农村建好后,余文海当上了村里的清洁工,每月 1000 多块工资,早上打扫卫生,每五天运一次垃圾。他还在附近的产业园打零工。

■ 横店村的标识。
村里的指示牌和墙壁上,到处印着余秀华的诗,从《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》到《我爱你》。不过,接受采访的十多位村民说“读不懂”。
立秋前,正是采收稻谷的时节。每到农忙时,余秀华就不愿出门。
她对这个村庄没有任何要求。村民做农活,余秀华不懂;她讲的东西,他们也不明白。她和村民谈不到一块,碰见了打个招呼,平常开个玩笑,互不影响。

■ 余秀华在旧居前。
村子的停车场变成了晒谷场。停车场对面是2018 年底建成的“余秀华旧居”景点,包括余秀华居住了四十年的四合院和一片竹林。余秀华已出版的诗集,描述的大多是在这里的生活印象。
奶奶住过的房间,以前塞满了东西,如今空空荡荡。屋顶加高了一尺,抬头便能看到新墙与旧墙的交替。
离旧居不远,门前贴对联、挂灯笼的便是余秀华的新家。家里没有狗、猫和兔子的身影,只有余文海养的两只鹅、两只鸭和十一只鸡(本来是十二只,后来死了一只)。
登上十层又十层楼梯,闻到淡淡的薰衣草洗衣液的味道,便到了余秀华的地盘。 二楼有三间房,余秀华住中间。 余文海住楼下,一般不上楼。 除非看不惯余秀华马马虎虎地打扫卫生,他才上楼一趟,边骂边擦。
2017 年母亲周金香去世,在荆门工作的儿子周末才回来。平日里,余秀华只有父亲作伴。
扫了一半地,余文海买了早餐,回屋给余秀华送上楼,自己则坐在餐桌边就着啤酒吃完。余秀华没吃他买的早餐,迷迷糊糊地下楼,摸到厨房,打开冰箱,颤颤巍巍地端出一盒冷冰冰的杂酱面。
除非有客人,余秀华一般不在餐厅吃饭,而是在后院一间墙壁被熏得黑乎乎的厨房里吃。余文海说余秀华吃饭老掉渣,这间屋没铺瓷砖,看不出来。
吃完早饭,余秀华又上楼躺下。
窗户下是正门,倚在窗边可以看见来往的村民。结婚时买的印有“喜喜”字的红毛毯,余秀华当凉被盖。床头柜上累着的书已落灰。机械手似的台灯定格在靠近枕头的上方,签字笔、插线板、碎屏的手机和卷页的书,散落在床上。
床尾一头对着两张并排的书桌,一高一矮。笔记本电脑落寞地待在小方桌上。镜腿处缠着橡皮筋的眼镜在一堆书旁极不起眼。这些书,一部分是出版社寄的,一部分是余秀华买的。
在余秀华的家里,找不到几本她自己的书。从2015 年1 月第一本诗集诞生起,余秀华一共出版了五本书,其中包括三本诗集、一本散文集和一本小说。第一本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和第二本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各卖出25 万册以上,另外三本的累积销量也不低于 30 万册。在诗集的印数普遍只有3000 本还卖不动的年代,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2020 年 9 月又加印了 3 万册。
余秀华无疑是当代最畅销的诗人。但她“那点小才华”不知是否遗传自父亲。
余文海念初中时,正值文革时期。贫下中农出身的他,被分配到生产队劳动,没再继续考学。他上学时爱看书,也爱写诗。余秀华曾捉弄过父亲,将他写的“顺口溜”全部发在了朋友圈,没想到获得一片赞赏。
她的脾气性格倒像父亲——诚实,感性,冲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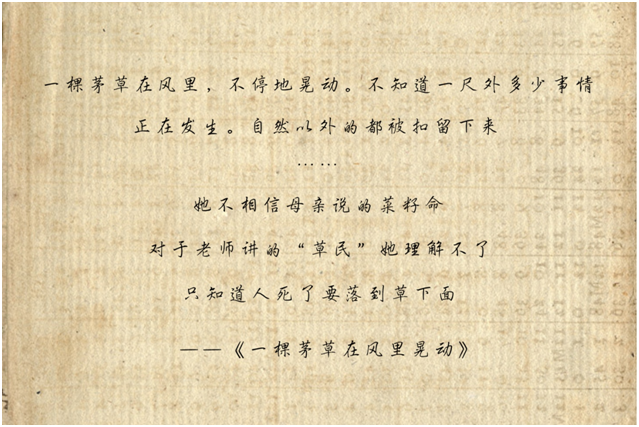
1976 年清明节,余秀华出生。家里请的接生婆没经验,余秀华倒产,小脑受损。由于缺少消毒设备,她还感染了破伤风,在荆门人民医院治疗了20 多天,才捡回条命。按照横店的习俗,每逢清明和春节,要给逝者上坟。在这一天来到人间,余秀华说自己像是“招鬼的”。
三岁时,余秀华躺在摇篮里坐不起来;直到六岁,她还不会走路。余文海和周金香求医问药,请神婆到家里做法事,都没起作用。算命的说,她前世做了坏事,这辈子要受罚。这些话在幼小的余秀华心里压了很久,“童年很恐怖”。
八岁上小学一年级时,余秀华还没有自由行走的能力。奶奶、母亲和父亲轮流背她上学放学。背了大概一学期,她开始练习杵双拐行走。
一年级期末考试,那天下大雪,余秀华没法到学校。因为缺考,老师让她留级。她和老师吵了一架。身体虽然不好,但记忆力好,她不觉得上学吃力,但最后还是留了一级。“雪”变作日后诗歌里挥之不去的意象。
三年级时,同学们嘲笑她杵着拐杖走路难看。她先甩了一根拐杖,不久后又扔了另一根,两只小脚丫学着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。有时,走到田埂走不动了,她索性往前爬。
到了四年级,学生们开始写作文。由于身体原因,余秀华没法控制手的稳定性。她必须用左手按着右手,一笔一划用力地写。手上起了老茧。
余秀华喜欢语文老师,写了封“情书”给她。老师当着全班念了,还表扬余秀华“写得好”。这是她文学的启蒙,也是鼓励,但仅此而已。80年代的农村,没有书店,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;即便有,余秀华也舍不得买。她找周金香要 2分钱买铅笔都要挨一顿批。
学校有个文学社,每月出一期小册子,所有学生可以参加。余秀华偷懒,觉得写文章太费事,投了首诗《无名星》,却得了一等奖。余文海读过那首诗,寥寥几句话:“她形容自己是一颗很小很小的星星。”
虽然得了奖,但余秀华的成绩赶不上努力。学习学不好,农活干不了。“无用”的她感到悲伤,觉得自己是家庭非常大的负担。“人活着,每天不进步不如去死。”初三那年,她拿起菜刀,割了左手腕。身体的包袱很沉重,直到今天还没消失。

■ 余秀华父亲余文海。
中考时,余秀华差了十几分。“她有勇气,跑到市里找校长。”余文海说。后来,学校没收任何费用,准许余秀华入学。
好不容易上了高中,却迎来人生最痛苦的日子。由于手腕弯不了,余秀华写字很慢,语文考试时,连作文都来不及写。“人家交卷了,她才写一半。”余文海说。
“我爸妈不了解我,他们觉得哪怕我读了大学也不会找到工作,因为我是残疾人。”余秀华是学校的保送生,校长承诺保她上大学;但不管怎么努力,成绩始终在下滑,她觉得对不起校长。到了高二,余秀华没参加期末考试就跑回了家。她收拢课本,一把火烧了。“一切都是自己搞砸的。”
父母确实没指望她上大学。他们在村里盘了一个小卖部,维持女儿的生计。
这时候,余秀华还没怎么写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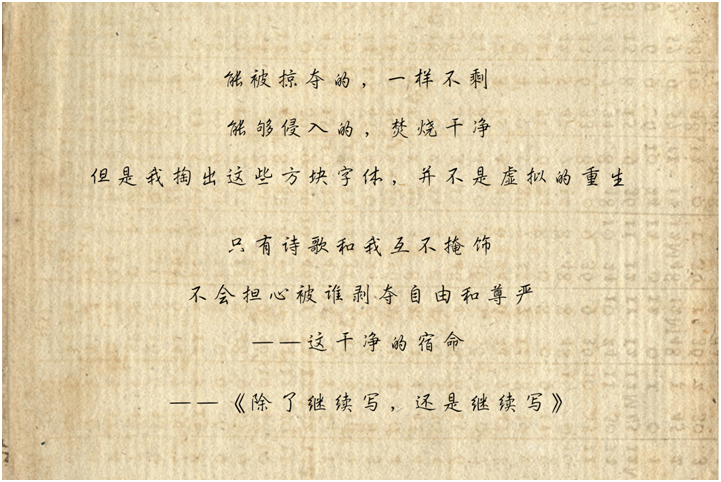
七月余秀华回家,八月就结婚。19 岁的孩子,还不知道婚姻是什么。
经人介绍,父母给余秀华招了一个上门女婿——从四川来荆门打工,比余秀华大12 岁的尹世平。父母叫余秀华去领结婚证。想着以后多一个玩伴,她就去了,“不知道还有婚姻生活、男女关系,一张白纸。”
结婚的时候,余秀华没感受到甜蜜,只担心那个男人会跑掉;生了孩子后,她巴不得尹世平跑掉。她想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,投入过这段感情,但发现没用,两人的精神世界不对等,没话说。
“结婚一年左右,她吵着离婚。”余文海说,“她是残疾人,老公是健全人,我们不许,她跟我们争,在炕上打滚。”
好在,尹世平常年在外,除开春节,一般不回家。两人虽然结了婚,却各过各的。他给余秀华留出了足够的个人空间。
守着小卖部,没人的时候,余秀华就拿个小本子写分行文字,当娱乐活动。邻居谢阿姨说,顾客来了,她写她的也不搭理,“卖不上什么东西。”
这期间,余秀华接触了不少社会青年。她跟他们下象棋、打扑克、骂脏话……年复一年,浑浑噩噩到了25 岁。
余秀华象棋下得不错,村书记比较欣赏她。有一天,他上门到余秀华家里下棋,翻到了柜子上写诗的小本子。他对余秀华说,你写得很好,要不要投稿?
投稿就要抄写诗歌,余秀华感到“痛苦”。但诗歌字数不多,她便试了试。投第一次,中了;投第二次,又中了。就这样,她的诗出现在当地的《钟祥日报》《荆门晚报》等报刊。不过,编辑们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。
上学的时候,她用右手写字。为练左手,她写了一篇10 多万字的小说。左手没有右手抖得厉害,字迹相对工整些。
这时候,余秀华写的诗也不多。

■ 余秀华旧居的大门。

■ 余秀华新居中养的花。
27 岁那年,周金香去儿子家帮忙带孩子,余文海既要种地还要打理鱼塘,小卖部没人照应,加上生意不好,就卖了。
没开小卖部以后,余秀华感到无聊,认真写起诗来。
当生活和心灵被逼上绝路时,没有任何人倾诉时,余秀华选择了诗歌。虽然她的双腿很难并拢,讲话含糊不清,表情也不自然,走路歪歪斜斜,但诗歌给了她灵魂的出口。
“迟早有那么一天,父母老了,丈夫靠不住,儿子有自己的家。”2012 年,渴望自力更生的余秀华背着父母,一个人坐火车去了温州打工。
工厂离海近,洗漱和吃饭的水要自己打,余秀华的手没力气,提不起重物,必须靠同事帮忙。工作间歇,她不和人闲聊,自个儿趴在床上写诗。“诗歌一直跟在身边,我想它的时候,它不会拒绝我。”
余秀华工作辛苦,“一天吃一顿,身体彻底垮了。”余文海给女儿打了很多电话,才把她追回来。余秀华做了一个月,因为动作慢,工资没挣到,还亏了300 多块路费。
为了自食其力,余秀华还跟着几个老头子讨饭。她买了一个碗,驻足了一天,但最终拉不下脸跪着,乞讨没做成。
吃的苦,受的伤,余秀华从来不告诉父母。余文海说:“她这人倔强,生病了全身冒汗,问她怎么了?她说没事。”余秀华却说,孩子生出来后是独立的个体,欢喜可以分享,但苦难没必要。
从 27 岁到38 岁成名之前,每到农忙的时候,余秀华心理都要遭受一次打击。九月和秋天,占据了她诗歌不小的篇幅。
2014 年,《诗刊》杂志编辑刘年在博客上发现了余秀华的诗。“她这样的作者,让编辑有成就感和幸福感。”没等余秀华回复,他就自顾自地选了几首诗,填了稿签。
通过 QQ 联系上余秀华后,刘年让她写一篇创作感想。“我是社会最底层的人,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生活。”余秀华心想反正没损失,爽快地同意了。
她在网吧只待了一小时,打了1000 多字的感想(超过一小时要多交三块钱)。在这篇题为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的短文中,她写下了一段话:“当那些扭扭曲曲的文字写满一整本的时候,我是那么快乐。”
2014 年 11 月杂志出来后,《诗刊》微信公众号也刊登了余秀华的诗。对一个当时关注数只有 2 万人的公众号来说,余秀华的诗创造了奇迹——阅读量超过了七万。随后,她的诗引发了转载潮。经学者沈睿推荐,网友推波助澜,《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》被转发了上亿次。
余秀华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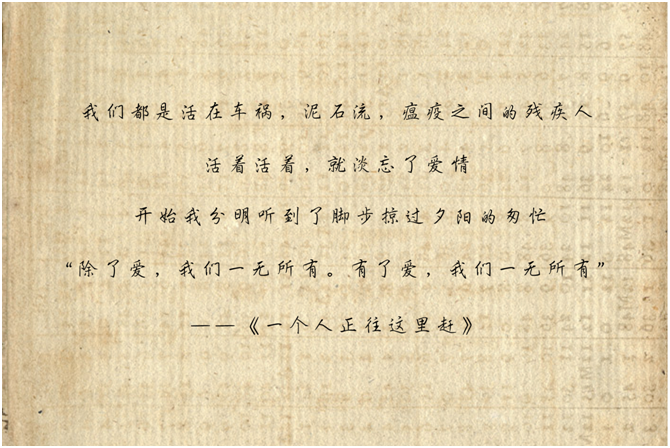
2015 年 2 月,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发行。余秀华收到第一笔版税,有了独立的本事。她下决心离婚。
尹世平收了余秀华给的15 万分手费。从民政局出来,两人吃了一顿“散伙饭”。
周金香得知女儿离婚的消息,气不过,连哭几天。余文海劝她:“有什么想不通的?是你女儿不要人家,不是人家不要你女儿。”
离婚后,余秀华和尹世平不来往。头几年,余文海叫女婿来家里团年,余秀华见了心里不舒服。2019 年春节,尹世平不来了。
虽然不怎么见面,但在父亲劝说下,余秀华用稿费给前夫在村里买了一栋房子,离自家不远,户主的名字只有尹世平。“他有个家,也算有根在这里。”她担心尹世平老了后,变成流浪汉。
“离婚是我一辈子做的最幸福的事。”刚离婚的那几年,余秀华快乐得要死,近两年又不行了。
身体给余秀华带来长期的痛苦,影响了她的感情走向。“有点能耐的人不会要她,没有能耐的人她也不要人家。”余文海说。
在感情上,她也主动过。17 年前,余秀华爱上了钟祥市的电台主播。成名后,那个人不再见她。20 多岁时,余秀华还敢跑到单位找他。现在的她不这么做了,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这段经历被她写进了小说《且在人间》。
和余秀华相处的人,大部分一开始觉得她可爱直率,相处久了又觉得她古怪,是泼妇。按余秀华自己的话说:“都是丑陋的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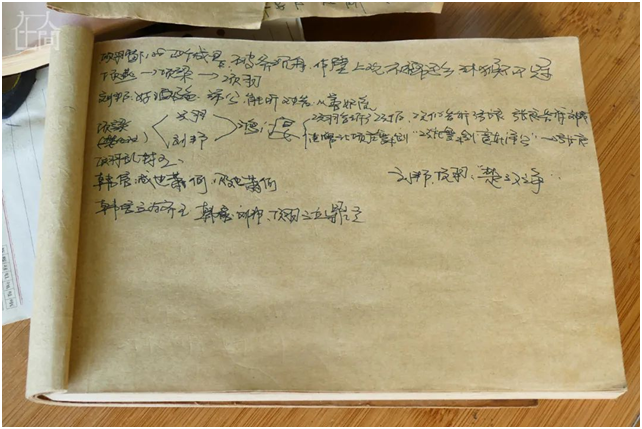
■ 余秀华的读书笔记。
余秀华害怕深层次的了解和交往,一贯的戏谑和调侃成为了她面对人世,“面对一切美好和恶毒的方式”。反而面对真正“爱”的人,她不敢见面,见了不敢说话,还要喝酒壮胆。
“当你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理由的,我无法判断所谓的理由是否总是带着一种不愿明说的目的性。喜欢一样东西,我说的是骨头里的喜欢,一定带上了先天性的属性,和生命的染色体有关。”她在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里写道。
年纪越大写得越好是余秀华的野心。好比新诗这个圈子,“有的写着写着就装逼。”去年和今年写的诗够出一本集子,但她觉得“出多了没意思,都是反复。”她希望“写得更好”。
然而,好是相对的,跟生活体验联系在一起。她知道哪些诗写得不好——偏激、疯狂、狭隘,这是她没打开的一部分。“打开的可能性很小。情执破不了,就没办法搞;情执破了后,有得有失。”
情是人一半的生命,破了之后魂丢了一半,可能成为一个智者“天天写诗”,也可能成为一个堕落者“天天喝酒。”但是,就没有爱情了。“没有一定想和谁在一起,为他吃不下、睡不着。情感都不要了,贞洁也毫无意义。今天睡一个,明天睡两个,后天睡三个……”
这个坎儿余秀华没过去。“女人败就败在爱情上。一个女人没有爱情,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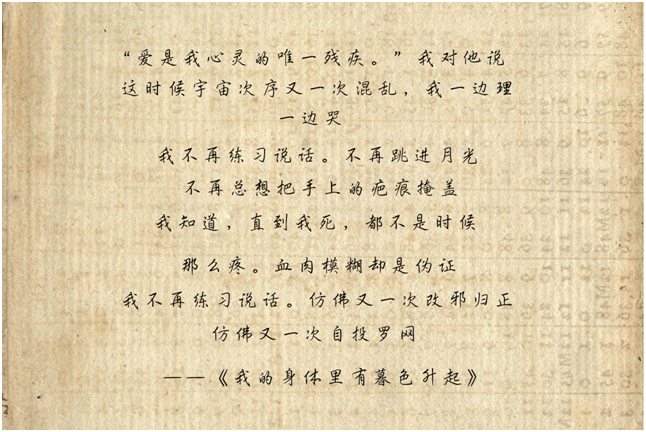
诗歌在生活里仿佛起不了作用。2018 年以来,余秀华到哪儿都睡不好。
平常她是开心果,可一旦遇到事情,两三个月走不出来。心情不好时,她容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。“诗人太分裂,既想当婊子,又想立牌坊。”
平静的心态才能写作。不能写的日子,余秀华靠喝酒打发时间。时间会消灭苦难,消解个人的苦恼。只要将时间打发过去,生命自然会起变化。
喝晕了,什么事干不了,读不了书,写不了东西,连好好睡一觉也做不到。尹世平爱喝酒,喝完后变着法跟余秀华吵架,实在令她厌烦。余秀华却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,“好在我喝酒不吵不闹,一个人趴在桌子上,醒了就滚床上去。”
可是,余秀华不控制自己,喝得快喝得多,一杯酒两三口没了。有两次,她因醉酒被送到医院。“打了一夜吊针才醒,真是让人担心。”余文海说,“搞过分的话,她能把自己毁灭。”
从小余秀华就不听话。余文海说:“她不挑事端,不发毛病,很好。她有时候搞些别出心裁的怪事,给你气死。”
家里买了一辆代步车,外型看上去像小汽车,但最快只有 50 码。余秀华坐了两次,研究了说明书后,趁余文海不备,偷了他放在卧室里的钥匙,独自上路了。绕着横店开了三圈,过下坡路时,她的脚使不上劲,刹不住车。车子撞到马路边的护栏,赔了 800 元。“幸好没伤到,也没有撞到人。”余文海想起就感到后怕。他把家里的酒锁在储物间,车钥匙也藏了起来。

■ 余秀华走在村道上。
2019 年,余秀华有一半的时间在生死线上挣扎。头发掉得凶,差点成一个秃子。她索性剃了寸头。
她觉得自己活不过,便找朋友在北京请了一位大师算命。大师说,余秀华的八字非常奇特,“相生相惜,相克相杀,不是好命也不是坏命。”尤为重要的一点是——余秀华能活到 80 岁,成为世界级名人。
“80 岁,怎么活啊?”余秀华发起愁来。她开始放心大胆地喝酒。她相信自己“半夜跳河自杀没人救,也会漂起来。”
有一晚在工作室,余秀华倒了两瓶劲酒在茶壶里,差不多两斤,不知不觉喝光了。星期天喝的,星期二才醒来,睡了两天两夜,“死掉了也不知道”。
她的腿是美的,却磕了不少伤痕,膝盖、大腿青一块紫一块。大多数伤是摔的。600 度近视的余秀华,嫌夏天太热,不怎么戴眼镜。看不见台阶摔,喝了酒摔,旧伤未愈,新伤又来,渐次成灾。
作为一个心灵敏感的人,内心总有不安。
每一次喝醉,眼睛没有流泪,但身体在哭泣。余秀华想:“我为什么活着?”不管身在何处、地位如何、有谁陪伴,孤独感始终如一。她幻想武侠小说的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:掉到山洞里,偶遇真经,一下子看破人生。但这终归是梦,是诗人迷幻的现实。
父亲余文海理解不了女儿:“她是瞎想,想得离轨。”有吃的有喝的,受人敬佩,在农村也算有钱,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?
余秀华却说,生死的问题并不会因为出名或有钱而得到解决。
一天中午,工作室只有余秀华一人。她拿了把水果刀放在枕头边,准备割腕。恰好,某报社的记者打来电话。他知道余秀华打算自杀后,骗她选一种不那么痛的方式——饿死。余秀华躺在床上等啊等,饿得受不了,又喝酒去了。
余秀华似乎有意弄疼自己,以此活得纯粹。“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,没有被酒精麻痹,没有被飘到半空的名誉的、侮辱的东西麻痹。”
到目前为止,编文学史的老师还没将余秀华的诗收入过,她也仅获得过民间文学奖。虽然对官方奖项不惦记,但余秀华还是希望获得鲁迅文学奖或诺贝尔文学奖,至少到那个阶段,她将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和尊重,以及更高的话语权。
诗人将这个世界看得很透彻,她可能因为绝望自杀,但不会因为诗歌自杀。“名誉和困境交织在一起,才心安理得。”
写不写诗,身体里的恐慌和伤害一直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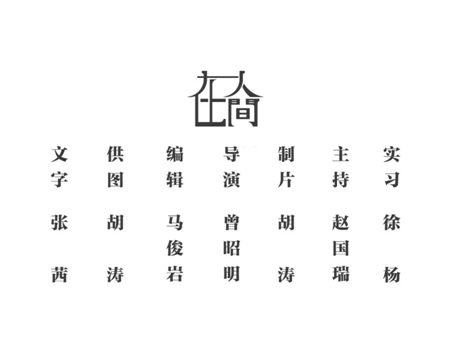
(来源:凤凰网)
